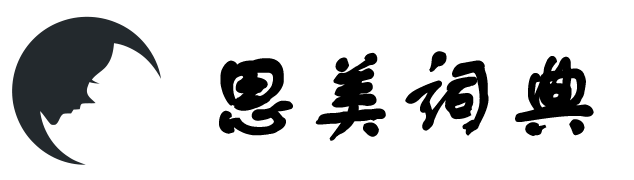我不下,我很担心。
「无碍,下去吧。」
男人总是嘴硬的,我不理会,自顾自地从领口钻进,爬过了胸膛,经过了小腹,终于明白了问题所在。
行一的身体在燃烧,从内往外,如即将迸发的火山口,带着能融化我的灼热。
许是我冰凉的身体略有缓解,他似舒服的叹息一声。
是以,我缠了上去。
「嘶……别……」
嗯?不对吗?
「对……不对……」
那晚,我在炙热与柔情里,见了行一最美的样子。
但我还是生气,与磨脱皮无关,也不是计较他消失了几天,而是……
「你明明听得懂我说话,却做了百把年的哑巴?!」
「你怎么忍得住的?!」
行一不作声,指尖带着股暖意抚过我身体,抚平了粗糙的蛇皮,指尖滑到我脑袋上轻轻一点,略有笑意。
「你终于发现了。」
合着,怪我蠢。
活该被你听了这么久的蛇女怀春。
3
我很想问问行一,我们这样算什么。
开口却怕玷污他,只问,「是山里的大妖想要取你阳气?使了下三滥的手段?」
「嗯,手段的确不高。」
那我懂了,「你也没有厉害到无所不能的地步。」
行一眼里倏尔涌动过一丝暗红,声音却空灵悠长。
「没有人可以无所不能。」
我当了真,想都没想就放弃了虚度年华。
除了每晚缠在行一腕间睡觉,其余时间都用来修行,我想……
不自量力的保护他。
奈何自己当真太蠢,四百年才隐隐有化形的征兆。
从前听蛇说过,初次化形虽然不疼,但过程有些丑陋,要生生将表皮撕裂后挣脱出来。
我不想行一看见。
便躲进了山林深处的干涸沟渠里,忍着冷意静待预料之外的痛感加深,直至临界点爆发。
细长的心脏生生压缩成碗口大小。
刺骨的寒意从心脏冻结往下,双腿淬了寒冰,我挣脱不开。
很冷,很疼,被骗了……
意识朦胧间,我听到了行一的声音,他在唤我。
「花梨。」
我本无名,有了行一,才有了存在的意义。
他是我的唯一。
我用尽全身力气还是来不及,被他看到了撕裂双腿的模样。
想必真的很丑,行一背过了身。
我低头看着不安的脚丫,忐忑中行一脱下白色僧袍,把我裹住后打横抱起,没有嫌恶。
步履如松间,搭在臂间的白嫩小腿晃晃悠悠。
「大师不怕抱错了人?」
行一眉梢一动,不置可否,我却不依。
「大师可认出了我是谁?」
行一笑了笑,「你在我房梁上盘了五百年。」
我们有五百年的纠缠不清,你却始终不明白,「那破庙是我先来的,怎就是你的房梁了?」
「哦?你先来的……」
行一低头瞧我一眼,语气平淡,「可那破庙是我建的。」
哈?
跳梁小丑原是我本人。
4
我和行一曾有过亲昵之举。
奈何懵懂间不曾回味过其中深意,我只记得他的美,以及脱了一层皮。
当行一将我抱放床上时,我竟下意识地扭捏不安。
「我才刚化成人形,可不可以等几天再化回去?」
行一不解,「为何要化回去?」
「缠不住……人形我不会……」
行一默了一瞬,抬手指了指床尾搁置整齐的衣裳后转身离去。
我才后知后觉自己说了什么胡话,咬唇拿过行一准备的衣裳穿戴整齐。
说实话,行一的眼光不怎么样。
哪个小姑娘喜欢穿得跟个和尚似的,一身披麻戴孝禁欲成仙。
行一也不喜欢。
他今晚看我的次数多了些,却离我很远。
我拍了拍床板,打断了他超长的诵经打坐,念得头晕。
「夜深了,大师你还不睡吗?」
行一睁开眼睛看我一眼,遂又闭上。
「你睡吧。」
「我冷。」
半响,行一一声轻叹,终是起身上了床。
我抱住他手臂舒服得叹气。
不知为何,我生来含霜格外怕冷,加之繆林山阴冷异常,冬天格外难挨。
蛇喜群居冬眠,而我却连父母都没见过……
我蹭了蹭行一肩头,「你真暖和,像个火炉似的。」
行一默不作声,任我抱着他手臂搓扁揉圆。
临睡前我问他,「挨着我冷吗?」
没有回答。
只在梦中的行一将我揽进怀中,带着微不可察的怜惜。
5
自打成精以来,山里的精怪不再躲着我。
甚至几些个男妖变了法的送东西讨我好,我笑得花枝乱颤。
「他们都说,想要俏,一身孝。」
「大师,我这样穿真如他们所说那样美?」
行一掀起眼皮瞧我一眼,「你穿的是僧衣。」
那又怎样,穿了僧衣又不代表要立地成佛,我嘟着嘴巴不理他。
半响,行一才悠悠道,「美的是你,与衣物无关。」
我不下,我很担心。
「无碍,下去吧。」
男人总是嘴硬的,我不理会,自顾自地从领口钻进,爬过了胸膛,经过了小腹,终于明白了问题所在。
行一的身体在燃烧,从内往外,如即将迸发的火山口,带着能融化我的灼热。
许是我冰凉的身体略有缓解,他似舒服的叹息一声。
是以,我缠了上去。
「嘶……别……」
嗯?不对吗?
「对……不对……」
那晚,我在炙热与柔情里,见了行一最美的样子。
但我还是生气,与磨脱皮无关,也不是计较他消失了几天,而是……
「你明明听得懂我说话,却做了百把年的哑巴?!」
「你怎么忍得住的?!」
行一不作声,指尖带着股暖意抚过我身体,抚平了粗糙的蛇皮,指尖滑到我脑袋上轻轻一点,略有笑意。
「你终于发现了。」
合着,怪我蠢。
活该被你听了这么久的蛇女怀春。
3
我很想问问行一,我们这样算什么。
开口却怕玷污他,只问,「是山里的大妖想要取你阳气?使了下三滥的手段?」
「嗯,手段的确不高。」
那我懂了,「你也没有厉害到无所不能的地步。」
行一眼里倏尔涌动过一丝暗红,声音却空灵悠长。
「没有人可以无所不能。」
我当了真,想都没想就放弃了虚度年华。
除了每晚缠在行一腕间睡觉,其余时间都用来修行,我想……
不自量力的保护他。
奈何自己当真太蠢,四百年才隐隐有化形的征兆。
从前听蛇说过,初次化形虽然不疼,但过程有些丑陋,要生生将表皮撕裂后挣脱出来。
我不想行一看见。
便躲进了山林深处的干涸沟渠里,忍着冷意静待预料之外的痛感加深,直至临界点爆发。
细长的心脏生生压缩成碗口大小。
刺骨的寒意从心脏冻结往下,双腿淬了寒冰,我挣脱不开。
很冷,很疼,被骗了……
意识朦胧间,我听到了行一的声音,他在唤我。
「花梨。」
我本无名,有了行一,才有了存在的意义。
他是我的唯一。
我用尽全身力气还是来不及,被他看到了撕裂双腿的模样。
想必真的很丑,行一背过了身。
我低头看着不安的脚丫,忐忑中行一脱下白色僧袍,把我裹住后打横抱起,没有嫌恶。
步履如松间,搭在臂间的白嫩小腿晃晃悠悠。
「大师不怕抱错了人?」
行一眉梢一动,不置可否,我却不依。
「大师可认出了我是谁?」
行一笑了笑,「你在我房梁上盘了五百年。」
我们有五百年的纠缠不清,你却始终不明白,「那破庙是我先来的,怎就是你的房梁了?」
「哦?你先来的……」
行一低头瞧我一眼,语气平淡,「可那破庙是我建的。」
哈?
跳梁小丑原是我本人。
4
我和行一曾有过亲昵之举。
奈何懵懂间不曾回味过其中深意,我只记得他的美,以及脱了一层皮。
当行一将我抱放床上时,我竟下意识地扭捏不安。
「我才刚化成人形,可不可以等几天再化回去?」
行一不解,「为何要化回去?」
「缠不住……人形我不会……」
行一默了一瞬,抬手指了指床尾搁置整齐的衣裳后转身离去。
我才后知后觉自己说了什么胡话,咬唇拿过行一准备的衣裳穿戴整齐。
说实话,行一的眼光不怎么样。
哪个小姑娘喜欢穿得跟个和尚似的,一身披麻戴孝禁欲成仙。
行一也不喜欢。
他今晚看我的次数多了些,却离我很远。
我拍了拍床板,打断了他超长的诵经打坐,念得头晕。
「夜深了,大师你还不睡吗?」
行一睁开眼睛看我一眼,遂又闭上。
「你睡吧。」
「我冷。」
半响,行一一声轻叹,终是起身上了床。
我抱住他手臂舒服得叹气。
不知为何,我生来含霜格外怕冷,加之繆林山阴冷异常,冬天格外难挨。
蛇喜群居冬眠,而我却连父母都没见过……
我蹭了蹭行一肩头,「你真暖和,像个火炉似的。」
行一默不作声,任我抱着他手臂搓扁揉圆。
临睡前我问他,「挨着我冷吗?」
没有回答。
只在梦中的行一将我揽进怀中,带着微不可察的怜惜。
5
自打成精以来,山里的精怪不再躲着我。
甚至几些个男妖变了法的送东西讨我好,我笑得花枝乱颤。
「他们都说,想要俏,一身孝。」
「大师,我这样穿真如他们所说那样美?」
行一掀起眼皮瞧我一眼,「你穿的是僧衣。」
那又怎样,穿了僧衣又不代表要立地成佛,我嘟着嘴巴不理他。
半响,行一才悠悠道,「美的是你,与衣物无关。」
本文出自思美词典网,转载需带上本文链接地址:http://www.simeijiachuangyi.com/juzi/216242.html